“從莫斯科(周邊)那幾個小鎮,謝爾吉耶夫,然後是蘇茲達爾,順序我已經不太記得了,然後到下諾夫哥羅德,那是高爾基的故鄉,然後喀山,伊熱夫斯克,就是AK47的(發明者)、槍王的家鄉,再到彼爾姆,然後葉卡捷琳堡、秋明,然後一個小地方叫伊希姆,然後再走到新西伯利亞。從新西伯利亞我們就坐火車,然後就到了伊爾庫茨克,然後到了北京。是這樣的一個線路。”
熱愛文學的李阿姨和任老師經常在文學作品中讀到關於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被流放到荒涼苦寒的西伯利亞的故事。他們本想沿著過去革命者的足跡去身臨其境地體驗一番,卻被西伯利亞的現代化發展所震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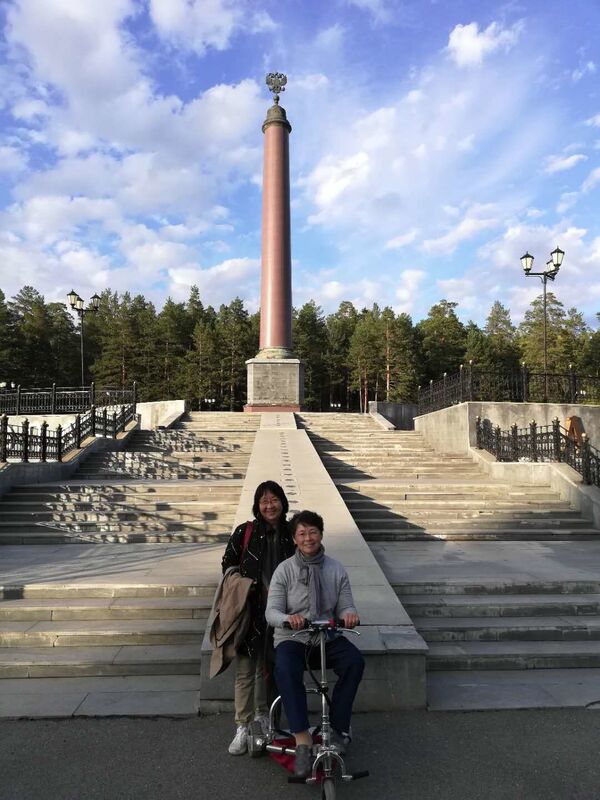
“遺憾的是,西伯利亞附近的城市我原來以為很荒,我喜歡那種很荒涼的感覺,因為看以前十二月黨人(和)妻子一路走過去,冰天雪地的。但是它仍然發展得很好,完全沒有了那種(荒涼)感覺。往東去的那些城市,有點像現在的中國,發展得是比較好的了。而莫斯科、聖彼得堡,是古城、古都了,不可能在裡面蓋高樓。但是你走到新西伯利亞這一帶,你會覺得它可能和過去是不一樣的。這個也是在歐洲其他國家看不到的。”
西伯利亞帶給80歲的任老師更多的是驚喜。
“最大的意外就是十二月黨人走過的所謂的‘苦寒地帶’。西伯利亞不要太美啊,哪裡苦寒啊。我都不想回來,想在那個地方買個木板房,我就住下了。”
雖然三人都不懂俄語,但李阿姨在出遊之前做了大量功課,她把俄語的33個字母熟記於心,並把一路上要經過的城市名、地名認真地記了下來。出行前,她收集了相當多的資料,把自駕會途經的城鎮及路線全部整理出來。最終,她製作出一本336頁的路書,共22萬6千字,裡面還包含海量圖片。李阿姨在自己的遊記中寫到,這本路書,光是用惠普噴墨打印機打印出來就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俄羅斯對於她,有著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親近感。
“大氣,這是一個,還有一個,怎麼說呢,對我們來說可能就是感情的問題,覺得這個地方是必須要去的一個地方,好像它是和我們有關係的一個地方。俄羅斯實際上也不是非常的高調,但是我們就覺得很奇怪,這麼一片土地上會出現那麼多的名人、大師。我們也說過,中國的孩子整天在搞素質教育,學小提琴,學繪畫,但是出了幾個大師呢?而俄羅斯你(可以)滿把滿把抓。各個領域都是這麼多的(大師)。甚麼都有,精神方面的,物質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太豐富了,實在是太豐富了。在新聖女公墓,我覺得就應該,就是不懂語言,要是懂語言的話,在裡面坐上三天、四天,慢慢地看,一個一個墓看,那就是一種享受,或者說是一種學習,一種瞭解。我覺得,(有句話)說的一點都不錯:俄羅斯的歷史一半在紅場,一半在新聖女公墓。那裡面的人太了不起了。”
新聖女公墓是三人俄羅斯之行最濃墨重彩的一筆。行前,李阿姨花了十來天的時間,查閱資料,用電子翻譯器將俄文轉成中文,再用中文專門整理出一份8萬字的新聖女公墓導覽指南。而對於同樣熱愛文學的任老師來說,能來到年輕時鍾愛的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前看一眼,表達她在那個單純年代里對文學偶像的敬仰之情,已是巨大的滿足。

“對我衝擊力更大的還是保爾·柯察金,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因為他本來就是書中的主人公,他自己又是作者,他有那麼多的經歷——小時候的貧窮,後來戰爭時期的堅強和堅韌,到身體殘疾了,還用另一種意志寫下好幾部小說。我們那個時候接受的就是這些東西。印象很深,覺得世界上最美好的就是這樣了。沒辦法看到他的故居,所以為甚麼要去看新聖女公墓呢?因為他的墓在那個地方。他的塑像跟我印象當中完全重合。我那天很想說兩句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但是我那天頭暈,我就沒寫,微信里就沒寫,這個是我個人的遺憾。但我終於對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雕像深深地敬了一個禮,表達我心中作為一個中國老人的敬意。從少年時代就開始了,終於完成了這個心願。”
“那個時候我們縣城裡面,老老小小,所有的人,對‘蘇聯老大哥’這五個字張口就出來,就蹦出來,很自然的。就是因為(他們)幫助我們了。我們穿的最時尚的布叫蘇聯大花布,唱的歌也是蘇聯的歌,讀的書也是蘇聯的書。那個時候,視野不開闊,讀書的條件不夠好,蘇聯又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又是從災難深重的苦難中過來的,突然就出現一個社會主義,以後就是共產主義(國家),誰都嚮往啊,那就是冬天的太陽一樣的,太美好,太有希望了。所以我們對蘇聯老大哥的感情深得很。”
當她看到俄羅斯的美好和偉大,會跟著欣喜,當她目睹有的人過得不那麼好,她會感到心痛。任老師說,這樣的情感並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而是一輩人的。年少時的他們曾經是那麼如飢似渴地閱讀蘇聯小說,邊讀邊做筆記。她身邊同齡的親人、朋友,無一不對蘇聯有著濃厚的感情,因為那是一個時代刻到個人身上的烙印。提到其他嚮往俄羅斯的老友,她說:
“只有跟團走,沒有人帶他們,但是他們一定要完成這個夢,一定要去看一下。我比他們幸運一點是自駕游,自由行,他們沒有這麼好的條件,其實情感都是一樣的,梳理一下,都是一樣的,濃濃的化不開的,對它有那麼一種依戀,很希望親近它,很希望到它的地方去看一下,感受一下,這個都是一樣的。”
在中國,很多人的內心深處都有著揮之不散的蘇聯情結。因為他們年少時讀的書,唱的歌,看的電影,都使這個遙遠國度成為心中的聖地、精神的故鄉,成為他們對未來的憧憬。80歲的任老師說,這是她生來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去俄羅斯了,但她非常滿足,因為她了卻了年少時的夢想。而對於李阿姨和丈夫來說,他們還想再去一次俄羅斯,看一看這次行程沒有來得及去的貝加爾湖,再次感受俄羅斯這個國家的美好和偉大。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5323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53235號